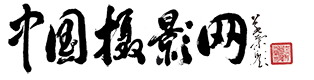▲《Saami Youthhood》©Natalya Saprunova(法国)
尽管她的头发是彩色的,口袋里装着智能手机,11岁的小女孩乌莉安娜还有很明显的萨米族特征,这是俄罗斯极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她喜欢户外活动、钓鱼、做手工艺品和刺绣。这些活动对她来说是继承游牧祖先的记忆。这些儿童游戏也体现了艺术的多样性。
乌利亚娜来自一个驯鹿牧民家族,由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人的定居,他们的传统几乎消失了。洛沃泽罗位于摩尔曼斯克市的腹地,是主要的萨米人集聚村,也是一个保护区。在萨米人的土地上也建立了其他村庄,以聚集驯鹿牧民。他们在kolkhozes安定下来,却再也不能成为萨米人了,因为他们不能说自己的语言,也不能穿着传统服装。
如今,乌莉安娜生活在大约有1500人的洛沃泽罗,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有时候木屋与混凝土建筑相邻。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她会去祖母家度假,祖母住在只有400名居民的小村庄里。她也会去拜访一位老妇人,后者是唯一一位还住在小村庄里的,有四座房子,不通电和自来水。这里仍然有一点旧世界的气息,当然也有一点新世界的气息。有一个强壮、开朗、动手能力强的女孩生活在这里,她可以抵御严寒以及成群的蚊子。
渐渐地,这种自然紧密联系的生活环境将会融入到乌莉安娜的血液中。这个11岁的女孩因此成为当地人民的记忆,一个可以在任何时候重生的记忆,就像乌莉安娜在石头上泼一点水就能让这些象形文字重新出现。一个面向未来的记忆在一个孩子的手中焕然一新。











▲《Sinfonía Desordenada》©Ana María Arévalo Gosen(西班牙)
委内瑞拉的管弦乐将极端贫困的年轻人从毒品和犯罪环境中解救出来,否则这些青年很可能会被卷入其中。这也是委内瑞拉管弦乐出名的原因之一。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崩溃,委内瑞拉管弦乐队的音乐家们无法靠他们的职业生存,而是需要从事副业。随着疫情的到来,他们工作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加。
委内瑞拉大马里斯卡尔·阿亚库乔交响乐团是复原力的典范。今年夏天,Elisa Vegas与Horacio Blanco合作,推出了一个名叫Sinfonía Desordenada的非传统项目。Elisa Vegas是委内瑞拉专业交响乐团唯一的女指挥,Horacio Blanco是一名曾获得格莱美提名的歌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精致的交响乐团中加入了一群摇滚乐手,在家里录制了一系列委内瑞拉斯卡乐队Desorden Público曲目中的一些经典的交响乐曲。关于如何录制这个问题,最不寻常的答案是:“用他们的手机"。在2021年11月,他们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隔离之后,见证音乐家们与观众一起演奏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从Elisa举起指挥棒的那一刻起,直到最后一个和弦的落下,这是一个庆典,一个治愈的时刻,一个希望的礼物。
实现这个项目需要巨大的勇气,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叠加疫情造成了额外的危机。它证明了音乐有一种复原力、治愈和建设社区的力量。












▲《Soul Searching》©Julie Kenny(澳大利亚)
对大多数人来说,2021年是激发反思和改变的一年。在教育领域工作了17年后,我开始质疑一切,包括教育系统和我在其中的位置,我的人生意义和选择。2022年,我请了一年假来寻找一些内心的平静,并评估什么能带给我幸福。
我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一些城镇长大,热爱探索自然美景、喝浓茶和闲聊。对乡村的尊重和风景所能承载的意义已经彻底融入我的内心。我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到遥远的地方旅行,尽情体验当地的文化并探索新的空间。我非常热衷于自驾旅行,因此,回到了故乡,探索故乡的美景,徜徉在西澳大利亚的不同景观中。
与乡村(Boodja)的联系是我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你开车经过较平坦的地区时,往往看不到风景的细节。我的摄影系列旨在分享我在探索过程中看到的惊人的颜色、纹理和图案。
虽然无人机摄影能够使用新技术来捕捉风景,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原住民记录这样的视角也已经有几千年了。












▲《Sport and fun instead of war and fear》©Mouneb Taim(叙利亚)
在叙利亚阿勒颇市附近的阿尔吉纳村,瓦西姆.萨托特为孩子们开设了一所空手道学校。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有残疾和无残疾的女孩和男孩都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年龄在6到15岁之间。
萨托特希望通过他的学校创造一种社区意识,并消除孩子们心中的任何战争经历,因为阿勒颇省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












▲《The Longest Way Home》©Antonio Denti(意大利)
《The Longest Way Home》是一个深刻的生存故事。
2022年,一个加拿大原住民代表团前往梵蒂冈,寻求教皇对教会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土著儿童在所谓的寄宿学校所遭受的虐待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道歉。这些在寄宿学校上课的孩子们强行与父母分离,并且被教导遗忘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以便进行同化和基督教化。
看到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等原住民代表穿着传统服装,在圣彼得柱廊下,等待他们的领导人从与教皇的会面中走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贝尔尼尼在1650年左右建造柱廊的时候,在大洋彼岸,法国和英国正在争夺加拿大的统治权,正是造成寄宿学校的暴力历史的开始。四个世纪后的今天,历史在柱廊下走到了一个清算的时刻。教皇说出了原住民几十年来一直渴望听到的那句话:"我很抱歉"。随后,广场的人们热泪盈眶,他们翩翩起舞来庆祝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
暴力和欺凌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产生相反的效果。反抗给予受害者重新征服自己的力量。这体现在梵蒂冈幸存者的身上。当他们从学校里走出来,找回原来的身份来反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行。他们更加热爱自己的身份背景,不仅仅活下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在大洋彼岸开始了艰难而必要的和解之路。












▲《The scatterd memories of a distorted future》©Maryam Firuzi(伊朗)
2020年1月8日,当听到乌克兰飞机在德黑兰被击落,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死亡的消息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绝望。从那时起,各种不幸事件接踵而来:政治动荡、水危机、经济衰退、我的家人和朋友的移民问题,以及其中最大问题:新冠疫情。每天早上醒来时,我感觉生活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似乎一切都成了废墟:我自己、家人、朋友、各种关系,城市、国家等等。
我们所承受的痛苦以废墟的语言表现出来。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所有这些痛苦(现在的语言)中,我希望找到通过艺术创作进行有效的治愈和激励的方式?艺术家对这个废墟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在建筑物的废墟上有还能扮演什么角色?
在这个系列中,废墟已经成为痛苦的隐喻。在这里,在沉默的过去和未知的未来之间,我邀请了女画家在废弃的建筑画上她们喜欢的东西;一幅关于男性历史的画,一幅关于过去的面孔的画,以及一个关于未来尚未解答的问题。